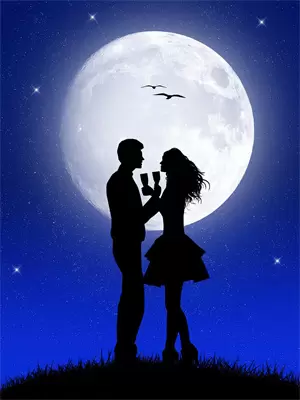我被老友坑去当一场大学辩论赛的评委。本想划划水就走,结果碰上个输不起的带队老师。
他当着几百人的面,公开指责我的评审标准有问题,就因为我看着年轻。
他以为我是个可以随便拿捏的软柿子。他不知道,我打辩论打到国家队的时候,
他可能还在读硕士。我不喜欢跟人吵架。我只是习惯把事实和逻辑,一字一句地,
重新摆回桌面上。让他自己看清楚,他和他引以为傲的队伍,到底是怎么输的。
1.那个看起来像实习生的评委我叫乔思,今天的工作是评委。大学辩论赛。校级的。
说实话,要不是徐冉那个家伙把我的绝版书扣下当人质,我才懒得来。下午三点,
礼堂里闷得像蒸笼。空调估计是坏了,头顶的风扇有气无力地转,
把嘈杂的人声搅成一团嗡嗡的浆糊。我坐在评委席最边上的位置。左手边是社科院的副院长,
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,正在闭目养神。再过去是赞助商代表,一个胖子,正低头玩手机,
屏幕光映得他满脸油光。我是第三个,也是最后一个评委。他们俩的桌上都摆着名牌:职务,
姓名。我的名牌上只有两个字:乔思。主办方问我头衔怎么写,我说写“青年学者”吧,
听着唬人。他们照做了,但看我的眼神,就像在看一个走后门进来的关系户。我理解。
我今天穿了件白恤,牛仔裤,帆布鞋,扎个马尾。桌上的保温杯里泡着枸杞。怎么看,
都像个来旁听的本科生,或者最多是个刚入职的辅导员。跟“评委”这两个字,
八竿子打不着。比赛开始前,两边的带队老师过来打招呼。正方的老师,就是徐冉。
他远远地冲我挤眉弄眼,嘴型说着“谢了”。我回给他一个“书拿来”的口型。
反方的带队老师,叫张承德,四十来岁,戴金边眼镜,头发梳得一丝不苟。
他跟副院长和赞助商握手,笑容很标准。路过我的时候,他的目光在我脸上停了一秒,
又迅速滑到我桌前的名牌上。那眼神里的疑惑和轻视,没藏住。他只是对我点了点头,
连手都懒得伸。我无所谓,乐得清闲,拧开保温杯喝了口水。
比赛题目是“科技发展是否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”。老掉牙的题目。正方,
也就是徐冉带的队,持方是“是”。反方,张承德的队,持方是“否”。比赛开始。说实话,
挺无聊的。学生们的水平,就那么回事。套路,全是套路。开篇立论,上价值,讲故事,
煽动情绪。我靠在椅子上,手里转着笔,有一搭没一搭地在评分表上画着。张承德的队伍,
风格很明显。气势足,语速快,排比句一套一套的,听着特有感染力。
现场的气氛很快被他们带动起来,掌声一阵接一阵。张承德坐在台下,
脸上带着稳操胜券的微笑,不时满意地点点头。徐冉那边,就显得“弱”很多。不怎么煽情,
就是慢悠悠地讲道理,摆事实。对面一个排比句甩过来,他们这边就一句“等一下,
我们来看一下您方刚才的数据来源”。场面上,完全被压着打。副院长已经有点昏昏欲睡了。
赞助商的手机游戏,估计都开第二局了。只有我,笔尖在纸上划动的频率,越来越快。
自由辩论环节,是全场的高潮。张承德队的一个短发女生,口才极好。“今天,
我们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,可以通过视频电话看到我们的脸,听到我们的声音,
这难道不是科技拉近了我们的距离吗?在座的各位,谁没有给家人发过微信,
没有在朋友圈为朋友点过赞?这每一条信息,每一次互动,都是科技为我们架起的桥梁!
对方辩友却视而不见,难道你们的心,是冰冷的吗?”一番话说得慷慨激昂,现场掌声雷动。
张承德在台下,带头鼓掌。徐冉的队员,一个戴眼镜的男生站起来,扶了扶眼镜。
他没急着反驳,而是问了一个问题。“请问对方辩友,您上一次和父母视频,是什么时候?
”短发女生一愣,显然没料到这个问题。“上……上个星期。”“那视频时长是多久?
”“大概……十分钟?”“好的,谢谢。那么在这十分钟里,您是把摄像头对着您的脸,
还是对着您的宿舍,给他们展示您新买的衣服,新换的床单?”短发女生脸色有点变了。
“这……这有什么关系吗?”“关系很大。”眼镜男生说,“科技让我们能‘看见’,
但看见不等于‘关心’。你展示的是你的生活,满足的是你自己的表达欲,
而你父母真正想看的,或许只是你的脸,想听你多说两句学校里的事。
科技给了我们一个高效的‘汇报’工具,却可能让我们忽略了真正的‘交流’。
我们用一张张照片,一段段语音,构建了一个‘我过得很好’的假象,
却让父母离我们真实的内心,越来越远。这,不是疏远又是什么?”全场安静下来。
张承德的笑容,僵在了脸上。我手里的笔停下,在徐冉队员的名字后面,
画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圈。有意思。终于有点意思了。2.一场毫无悬念的胜利比赛结束了。
双方四辩做总结陈词。张承德的队伍,那个短发女生,最后还是回到了煽情的老路。
讲自己在外求学,讲父母在家乡的牵挂,讲科技如何慰藉了思念。声情并茂,眼眶都红了。
不少观众,特别是大一的新生,都被感动得稀里哗啦。掌声经久不息。轮到徐冉的队伍。
还是那个眼镜男生。他没讲故事,只是平静地复盘了整场比赛。“尊敬的评委,主席,
各位同学。今天我们讨论的,不是科技的好与坏,而是它对人际距离的真实影响。
”“对方辩友一直在用‘连接’的数量,来论证距离的‘拉近’。微信好友五百个,
朋友圈一天上百条,这就是拉近吗?”“我们认为,距离的远近,不取决于信息传递的频率,
而取决于信息传递的深度。”“科技让我们可以轻易地进行浅层连接,点赞,评论,
发个表情包。但同时,它也可能剥夺了我们进行深层沟通的耐心和能力。
”“我们习惯了用15秒的短视频去了解一个人,习惯了用‘在吗’开始一段对话,
习惯了在屏幕后面表达廉价的关心。”“我们看似和所有人都保持着联系,
实际上可能和任何人都未曾真正靠近。”“科技给了我们无数个窗口,
让我们看到别人想让我们看到的世界。但真正的交流,需要推开门,走进去,坐下来,
面对面。”“我们得到的,是连接的便利。我们失去的,可能是连接的温度。”“所以,
我方坚持认为,科技的发展,在某种程度上,疏远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。它给了我们幻觉,
却拿走了实质。谢谢大家。”没有一句煽情的话。没有一个华丽的词。他说完,
对着评委席鞠了一躬,坐下。全场安静了几秒钟。然后,掌声响起来。比之前任何一次都响。
是那种发自内心的,思考过后的掌声。我靠在椅背上,把手里的评分表,
递给了旁边的工作人员。胜负已分。毫无悬念。评委退席,到后台的小会议室里合议。
工作人员给我们倒了茶。副院长清了清嗓子,率先开口。
“这个……反方张承德队气势很足啊,现场效果很好嘛。
”赞助商胖子附和道:“对对对,那个小姑娘最后讲得我都快哭了,多感人。
”他俩显然没怎么认真听。副院长看向我,带着一种长辈对晚辈的考教口吻。“小乔老师,
你怎么看啊?”我放下茶杯,杯底和桌面碰撞,发出清脆的一声。“我选正方徐冉队。
”我说得很平静。副院长“哦?”了一声,有点意外。“说说理由。
”赞助商也好奇地看着我。“辩论比赛,评判标准有三。第一,论证责任;第二,
逻辑交锋;第三,价值升华。”我没看他们,只是看着桌上的评分表。“第一点,论证责任。
反方的立论基础是‘科技提供了连接的工具=拉近了距离’。但他们整场都没有论证,
为什么‘连接’就等于‘拉近’。这是他们的核心论证义务,他们没有完成。
正方抓住了这一点,并且提出了自己的标准,‘深度沟通’才是衡量距离的标准。标准一出,
高下立判。”“第二点,逻辑交锋。整场比赛,反方都在用个例和情绪,
来回避正方的核心质疑。最典型的就是自由辩论环节,正方问视频通话的‘质量’,
反方却一直在强调‘有’视频通话这件事本身。这是典型的偷换概念。
正方始终在逻辑框架内打,而反方,早就打飞了。”“第三点,价值升华。反方的总结,
落点是个人情绪的宣泄。而正方的总结,把议题从个人感受,
提升到了对整个时代社交方式的反思。格局不一样。”我讲完,端起茶杯,吹了吹热气。
会议室里很安静。副院长的表情有点尴尬,他没想到我这个看起来像学生的年轻人,
能说出这么一套东西来。他干咳了两声,“嗯……小乔老师说的,很有道理,很专业。
”赞助商在旁边一个劲儿点头,看我的眼神都不一样了。“专业,太专业了。
我听着都觉得是正方厉害。那就正方,我同意。”副院长顺水推舟,“好,
那我们就统一意见,获胜方是正方。”结果就这么定了。我们回到礼堂,
主持人正用激动人心的语调暖场。看到我们回来,他立刻提高了音量。“现在,
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,欢迎评委老师回到席间!比赛的结果,即将揭晓!
”我坐回自己的位置。不经意间,我瞥了一眼台下的张承德。他正看着我,
眼神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审视和……敌意。他大概猜到了。在三个评委里,
那个看起来最没用的我,才是决定他命运的关键。3.这位老师,
请坐下主持人开始宣布结果。“下面,我宣布,
本次大学辩论赛的获胜队伍是——”他故意拉长了声音,台下的学生们都屏住了呼吸。
张承德的队员们,脸上带着紧张又自信的笑容,甚至已经有两个人悄悄地握住了手,
准备欢呼。“正方代表队!”声音落下的瞬间,礼堂里一半是错愕,一半是惊喜。
徐冉的队员们愣了一秒,才爆发出巨大的欢呼,几个人激动地抱在了一起。而另一边,
张承德队员脸上的笑容,瞬间凝固。那个短发女生,眼圈一下子就红了,
不敢相信地看着评委席。张承德的脸色,黑得像锅底。他放在膝盖上的手,猛地攥成了拳头。
主持人还在走流程:“下面,有请社科院的刘副院长,为本次比赛做点评。”副院长站起来,
拿起话筒,讲了一些场面话。“同学们都很优秀……比赛很精彩……友谊第一,
比赛第二……”他大概讲了五分钟,滴水不漏,但什么实质内容都没有。点评结束,
本该是颁奖环节。就在这时,一个不和谐的声音响了起来。“等一下,刘院长。
”张承德站了起来。他手里拿着一个话筒,不知道什么时候从工作人员那里拿的。
全场的目光,瞬间聚焦在他身上。“我对这个比赛结果,有异议。”他一字一句,
说得很大声。礼堂里顿时一片哗然。输了比赛,当场质疑评委?这种事,很少见。
太不体面了。徐冉在台下皱起了眉,冲我递了个眼神,意思是“你看,来了吧”。
我面无表情,静静地看着张承德。看他要演哪一出。副院长显然也没想到会这样,
拿着话筒有点不知所措。“张老师,你……你这是什么意思?”张承德推了推眼镜,
目光直直地射向我。不是副院长,也不是赞助商,就是我。“刘院长,我不是质疑您,
也不是质疑赞助商代表。”他把话挑明了。“我只是觉得,一场专业的辩论赛,评委的构成,
也应该足够专业。”“我们学校的辩论赛,一向有自己的风格和传统。
我们注重的是逻辑的严谨,更是语言的感染力,是辩手在台上的激情和风采。
”他开始拔高自己的队伍。“我的队员们,整场比赛气势如虹,引得全场掌声不断,这一点,
在座的各位都有目共睹。反观对方,四平八稳,毫无亮点。我不明白,我们到底输在了哪里?
”“所以我怀疑,是不是有的评委老师,评审标准……有失偏颇?”他最后四个字,
咬得特别重。“有失偏颇”。矛头直指我。因为我年轻,因为我的名牌上没有头衔,
因为我看起来最“不专业”。他觉得,是我这一票,导致了他的失败。他觉得,
我是个可以随便拿捏的软柿子,只要当众施压,我就可能心虚,会出丑。到时候,
他就可以把输掉比赛的原因,归结为“评委不公”。他的算盘,打得真响。
礼堂里安静得可怕。所有人都看着我。学生们在交头接耳,眼神里充满了好奇和八卦。
我的队员们,脸上是愤怒和担忧。副院长和赞助商,则是一脸的尴尬。张承德的队员们,
特别是那个短发女生,看着我,眼神里充满了委屈和怨恨。
仿佛我偷走了本该属于她们的胜利。主持人站在台上,急得满头大汗,不知道该怎么办。
我没动。我甚至连坐姿都没变一下。我只是静静地看着张承德,等他说完。等他把所有的戏,
都演足。他看我不说话,以为我怕了。他更加来劲了,声音也更大了。“我希望,
评委老师能给我们一个解释。一个公开、透明、公正的解释!否则,我们不接受这个结果!
”“对!不接受!”他的队员在下面喊。气氛,被他煽动到了顶点。压力,
全部来到了我这边。副院长小声对我说:“小乔老师,要不……你简单说两句?”他的意思,
是让我服个软,打个圆场,把这事糊弄过去。我没理他。我拿起了桌上的话筒。打开开关。
“滋——”的一声轻响。全场的目光,像探照灯一样打在我身上。我看着台下的张承德。
开口了。声音不大,但通过话筒,清晰地传到了礼堂的每一个角落。“这位老师。
”我连他的姓都没叫。“请问,您是想听我解释,还是想听我……复盘?”张承德一愣。
他没想到我会这么冷静。更没想到,我会用“复盘”这个词。解释,是示弱。复盘,是审判。
“你……你什么意思?”我笑了笑。很淡的笑。“我的意思是。
”“如果你只是想要一个台阶下,那我可以给你。”“但如果你真的想知道,
你们为什么会输。那我也可以告诉你。”“现在,你选。”我的声音很柔和。
但在寂静的礼堂里,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。张承德的脸,涨成了猪肝色。
他被我架住了。他说要解释,现在我把选择权交给他。他要是选了“台阶”,
就等于承认自己是在无理取闹。他只能硬着头皮说下去。“我当然是想知道,
我们为什么会输!”他几乎是吼出来的。“好。”我点了点头。然后,我站了起来。
一手拿着话筒,一手拿着那张写满了记录的评分表。我环视全场。最后,
目光落在张承德的脸上。“那么,这位老师。”“还有在座的各位同学。”“请准备好。
因为接下来的十分钟,可能会打败你们对这场比赛,甚至对辩论的认知。”“现在,
我们开始复盘。”4.复盘上:谁的论证责任?我拿着话筒,走到了评委席的前面。
这样,我可以面对着全场所有的观众。礼堂里,连一根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能听见。
所有人都看着我。张承德站在台下,双手抱在胸前,
摆出一副“我看你能说出什么花来”的表情。他的队员们,也都昂着头,一脸不服气。
我没看他们。我的目光,落在了他队里的一辩,一个戴眼镜的男生身上。“首先,
我们从比赛最基础的层面开始。也就是,论证责任。”“辩论不是吵架。不是谁声音大,
谁有气势,谁就赢。”“辩论的核心,是逻辑。而逻辑的起点,
是承担起你对自己立场的论证责任。”我顿了顿,给了大家一个吸收信息的时间。
“本场比赛,反方的持方是‘科技发展疏远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’。张老师,对吗?
”我把问题抛给了张承德。他愣了一下,下意识地点头:“对。”“很好。
”我按了一下手里的激光笔,一道红点打在了身后的大屏幕上。屏幕上,
瞬间出现了反方一辩立论陈词的PPT。这是主办方准备的,没想到现在派上了用场。
“反方一辩,在开篇立论时,提出了三个分论点。第一,科技让沟通变得肤浅。第二,
科技造成了信息茧房。第三,科技替代了真实陪伴。”“听起来,逻辑严密,无懈可击。
对吗?”台下一些支持反方的学生,下意识地点头。张承德的脸上,也露出了一丝得色。
我笑了。“但是,你们从头到尾,都回避了一个最核心的问题。”我的声音,
陡然变得清晰而有力。“那就是,你们对‘疏远’的定义是什么?”“你们的标准是什么?
是沟通频率降低了,算疏远?还是沟通时间变短了,算疏远?还是沟通的满足感下降了,
算疏远?”“你们没有说。你们默认了一个模糊的、情绪化的概念,
然后用一堆看起来很有道理的例子去填充它。”“这就好比,你想证明一个东西‘不好吃’。
结果你上来不谈论它的味道、口感、食材,而是大谈特谈厨师的衣服不干净,
餐厅的装修有问题。你的论证,从一开始,就偏离了靶心。”“所以,你们的三个分论点,
本质上是三个漂亮的靶子,但它们都立错了地方。你们整场比赛,都在对着空气开枪。
”我的话音刚落,台下响起了一片小声的议论。很多学生,露出了恍然大悟的表情。
张承德的脸色,开始变了。我没理他,继续说。“反观正方。他们在立论的时候,
就给出了自己明确的定义。他们认为,‘距离的远近,取决于沟通的深度’。
并且给出了衡量的维度:是否增进相互理解,是否带来情感支持。”“这是一个可以被衡量,
可以被讨论的标准。”“有了这个标准,他们的论证,就有了根基。他们后面所有的例子,
无论是视频通话的质量问题,还是朋友圈的点赞社交,都是在围绕这个核心标准展开。
”“他们不是在打靶,他们是在建楼。”“而反方,从头到尾,
都在试图去推倒一栋他们自己幻想出来的,根本不存在的楼。”“这就是论证责任的失败。
”“张老师,我这么说,您能听懂吗?”我再次看向张承德。他的嘴唇动了动,想反驳,
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因为我说的,是事实。是辩论最底层的逻辑。他可以不懂,
但他不能否认。我没等他回答。“这只是第一点。”“接下来,我们谈第二点。
也是辩论中最精彩的部分。”“逻辑交锋。
”5.复盘中:无效的交锋与致命的躲闪我按动手里的激光笔,
屏幕上的PPT切换到了自由辩论环节的记录。是我自己画的简易逻辑攻防图。箭头,线条,
关键词,一目了然。台下的学生们,很多都拿出了手机,开始拍照。
“我们来看整场比赛最激烈,也是观众看得最过瘾的自由辩论。”“张老师的队伍,
在这一环节表现得非常强势。语速快,反应快,抛出的问题一个接一个,
让对手几乎没有喘息的机会。现场效果,非常好。”我先扬后抑。
张承德的脸色稍稍好看了一些。“但是,”我的话锋一转,“强势,不等于有效。
”“我统计了一下。在八分钟的自由辩论里,反方一共提出了21个问题。
而这21个问题里,有15个,是无效问题。”“什么叫无效问题?”“比如,你们的二辩,
反复追问正方三辩,‘你难道不给你的父母发微信吗?’。这个问题,就是典型的无效问题。
因为它和你们的核心论点没有任何关系。正方承认使用科技产品,
并不能证明科技拉近了距离。”“这就像打拳击,你一顿组合拳打出去,看着虎虎生风,
结果拳拳都打在空处。除了消耗自己的体力,没有任何意义。”“而你们,花了整整五分钟,
在这种无效的攻击上。”我看着反方的辩手们。他们的头,已经渐渐低了下去。“现在,
我们再来看正方。”“正方在自由辩论里,只问了7个问题。”“但这7个问题,
个个都打在了你们的七寸上。”我把红点,聚焦在逻辑图的一个关键节点上。“最致命的,
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个问题。‘你上次和父母视频,是展示你的生活,还是关心他们的生活?
’”“这个问题,直接击穿了你们用‘科技连接’构建起来的温情脉脉的假象,
触及到了问题的核心——连接的质量。”“面对这个问题,你们的四辩,是怎么回答的?
”我看向那个短发女生。她下意识地避开了我的目光。“你的回答是,‘这有什么关系吗?
’。”“然后,你就开始回避,转而去攻击对方辩友‘冷血’‘不孝’。
”“这是一次致命的躲闪。”“在辩论场上,当你开始攻击对方的人格,
而不是回应对方的逻辑时,你就已经输了。”“因为这说明,你在逻辑上,已经无路可走。
”“你试图用道德绑架,来掩盖你的理屈词穷。”“从那一刻起,你们的阵地,
就已经被攻破了。后面所有的反抗,都只是在被占领的高地上,徒劳地挥舞旗帜而已。
”我的声音不高,但每个字都像锤子,一下下敲在张承德和他的队员心上。那个短发女生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