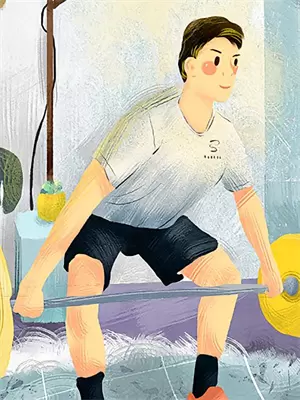
三岁那年,母亲牵着我,穿过重重宫门。明黄瓦、琉璃盖,朱红墙,白玉栏,耀目新奇。
凤座上那个威严美丽的女子冲我招了招手,温柔一笑,眉目慈爱:“阿缨,来,
到表姨母这来。”我颤颤巍巍地伸出了手,至此成为了她最宠爱的小辈,博弈的筹码。
只是一颗棋子,不该生了违背执棋人的心意。我偏偏爱上了局中弃子,成王二公子林瑾。
我鼓起勇气为心中所属之人重开新局,却被他一句“不合适”打得节节败退。我心如死灰,
嫁给了成王府世子林瑜。也许是红颜薄命,婚后不消两年便香消玉殒。葬礼上,他凯旋而归。
似入了障般地要我回来,开始创飞每一个伤害过我的人……1天阴沉沉地飘起了细雨,
圆白冥币飞坠在湿重的空气中,被雨打落满地。白色的招魂幡随风舞动,人声交杂着细雨,
喊着魂兮,安兮~今天是我的出殡的日子。梨花棺木入了王陵,
那些感念成王公爹在外抗敌替送葬的百姓到了城郊外就已止步。王陵内只剩王府之人,
及家中亲人。我的夫君林瑜站在棺前,一身齐衰白服,形貌憔悴。脸上是悲痛欲绝的神色,
恨不得要同我一起离去。皇城中人皆知,成王府世子仙人姿貌,生得风流,却是个情种,
只钟爱一人。那人便是我,昌阳县主,阮缨。为了娶我,
他淋着大雨在太后的安寿殿前跪了整整三夜,送了半条性命才换得太后松口赐婚。葬礼将成,
他的手眷恋摩挲在我那发白如纸的面颊上迟迟不忍离去。周遭的人都在劝慰,逝者已矣,
生者节哀顺变,盖棺安息。可他仍旧不闻,双目赤红一副情深不寿的模样看着棺内的我。
而我的魂魄就在他身侧,如狂风吹不皱的水面,一丝涟漪未起。2身边的人一催再催。
棺盖将将合上的那一刻,一支利箭破空而来。箭矢硬生生扎进了青砖碎裂的缝隙之间,
林瑜的手也被划破,合棺的动作被迫停止。他一脸惊恐慌乱趴坐在地,
同惊慌的众人朝箭来的方向看去。银衣铠甲,风尘仆仆,一人持弓而立,眉目凶怒。
我心里一阵震动。恍惚地看着面前那个人,那张华丽的弓。只听王府管家惊喊:“瑾公子?
”林瑜回神,眼里闪过一丝怒意,又很快恢复了悲伤的神色。他站了起来,朝林瑾走去。
“二哥,你回来了。”音色难掩伤心却又恰到好处地带上了些对亲人的依赖。林瑾似未察觉,
或者说是忽视。他的眼,只定定地看着那副留有一掌间隙的梨花棺,失魂向前,
欲伸手推开棺盖。“二哥!”林瑜惊呼,拉住了他。“三……世子,小心。”霎时间,
弓弦就抵在林瑜白皙的喉骨。那一声娇柔的提醒,是我的妹妹,阮纭。林瑾凶神一般看着他,
眼里俨然有了杀意。此时,众人的注意力都被林瑾出格举动给吸引,
没人留意到阮纭话里的诡异。只有林瑾扫了她一眼,嘲弄冷笑,“三世子……姨妹,
你这称呼,可真是别致~”众人这才觉不对,纷纷看向阮纭。阮纭面红耳赤,
知自己情急之下喊错了话。她该喊林瑜“姐夫”或是世子才合理数,
而不是什么不伦不类的三世子。我冷冷一笑。见她眼眶有泪摇摇欲坠,
葱白的手绞着擦泪的绢帕,“我只是……”一副楚楚可怜欲说还休的模样。
“我只是一时间接受不了姐姐离开的事实,又被二公子的举动吓到才会口不择言。
”说完眼泪跟着就掉了下来。3美人垂泪,我见犹怜。我这妹妹生得冰肌玉骨,
行止弱柳扶风,是皇京中数一数二的琉璃美人。她一哭,显林瑾的举止形容更似凶煞恶兽,
让人心生可怖。生前我以为她是无骨的丝花,需要攀附才能存活。阮纭是外室女,
生母死后才入的府。从前我便是被她这梨花带雨的模样所欺,背着母亲私下没少对她关照。
如今再看,一切都是她驱使人心的惯用伎俩。没有人再深究一个受惊美人的错处,更有甚者,
替她出头。林瑜跳了出来,“二哥,阿缨身逝,我知你难过。可她毕竟是我的妻,
你如今这般,未免有失王府体面。”带着愠怒和得体出言相劝。“体面?”林瑾漠然一笑。
手腕轻动,一丝细细的红线从林瑜白嫩的脖颈儿汨出,他吃痛地“嘶”了一声。
那弓弦是我派人踏遍大江南北,寻了大半年才找到的冰原蚕丝。蚕丝捻成的弓弦极细极韧,
尤其是林瑜这种皮肤吹弹可破的,用对了巧劲可杀人于无形。见了血人群传出一阵骚动。
阮纭更是惊呼地“啊”了一声,仿若见鬼。林瑜随即大喊:“林瑾,你疯了吗?
”隔断了一切不安的躁动。空气凝结,针落可闻。林瑾却宛如地狱里重生的恶鬼,翩然一笑,
眼里没有任何温度。他一步上前,凑近林瑜耳边,轻答:“我是疯了,
从知道她死讯的那一刻,我就已经疯了!”而那一句轻声低语,
顿时让林瑜身侧的我魂灵震荡。4三年前,烨国得到密报,之前归顺烨国的朔月受枭国唆摆,
又开始频频搅扰我国北面州郡。为防北地兵变,镇国军主帅成王林骁奉皇命,领长子林琮,
次子林瑾同镇国军一并北上驻军。得知消息时,已是出征前日。我匆匆托了林瑜,
约林瑾在新月楼相见。那日,京中暴雨,等了许久才见林瑜拉扯着林瑾进来。
林瑜担忧地看了眼我,不厌其烦地道:“你们好好聊,我就在隔壁,有事喊我。
”那时我把他当做好友,不耐地应了一句“好”,不客气地将他赶了出去。偌大的厢房内,
仅剩我和林瑾。万千思绪我从脑海中闪过,一时间不知从何开口。是他先开打破的沉默。
“阿瑜说你有要事找我?”我抬头看他。见他眉目间神思疲惫,
徘徊在心里的那句“为何不告知我你要出征北上”便咽进了心里。又替他找好了理由。
他的生母冯侧妃月前刚殁,想来是还未走出伤痛又出征,诸事烦杂才未顾及。
我抛开那些矫情别扭的情绪,冲他一笑,而后问道:“此番北上,你会带上如愿,对吗?
”如愿是把弓,是我送他的第一份生辰贺礼。送礼时他曾说过,若将来去了战场,
定会带上如愿,一起名扬天下。所以问出这句时,我心里早已有了确切的答案,
只等他说“会”。只要他说,我就敢奋力一搏,细细筹谋,推拒掉太后早就为我铺好的路。
在皇京等着他,等着他带着如愿名扬归来娶我……哪知他开口,说的却不是心中所想的答案。
5“如愿太过贵重华丽,不适合带去浴血搏杀的战场里。”他神色淡淡,语调极轻。
我心仿若被什么重重的垂了一下,故意忽视他的弦外之意,溺水中挣扎。
“此前你不是……”话还没说完,他端正的站了起来,抱拳行礼,打断了我的话音。“县主,
那时是臣年少妄言,还望县主不要放在心上。”县主,臣……我握紧了拳,
心里的火气猛然升腾,“年少妄言,很好!”沉着脸继续追问,“既如此,
那我便再问林二公子一句,你我相知一场,是否幼年时说过的话,发生的事全然都不作数!
”年少的岁月里,他曾答应过我许多许多的事。比如要带我去看最美的梨花盛景,
同我酿最好的梨花白。再比如年年生辰都会和我一起放灯祈愿,庆贺彼此生辰。
又再比如说好了不会惹我生气,会一直一直护着我……我一瞬不瞬地看着他,迫他回复。
他神情烦躁扫了我一眼,“县主,年幼的话自然作不得数,将来你会是我阿嫂,
阿瑾自会敬你重你,但县主若求其他,恕阿瑾不能,更不愿!
”没想到我的一再追问换来的是阿嫂和不愿,何其讽刺!与林琮阿兄婚事,
是太后牵制成王的棋。是棋皆有变数。我本是带着破局的变数而来,
却被人当头浇下了一盆冷水。心冷如冰的我拔下了特意簪在头上的一溪月,
这是他送我的第一份生辰礼,是情谊是缠绕的起始。“林瑾,今日以此簪为证,
至此之后我们再无瓜葛,阴阳不犯。”玉簪啐落在地恍如昨日,形如你我,从此决断。路,
明明是你选的!你为何又带着如愿出现,发了狂,懊恼悔恨?6回忆片刻,
如愿的弓弦再入了林瑜红肉半寸。若不是当时林琮阿兄及时赶到,夺了林瑾手中的弓,
也许现下林瑜便是一具冰冷的死尸。若是那日他死了,现下哪里还有机会在书房的密室之中,
与我的好妹妹浪海沉沦,折磨着我的耳朵。打从招魂复礼过后,我的魂魄就离不了林瑜太远。
室内红浪声一浪高过一浪,偏偏我死后听力极佳,就算现在五丈外,也能听得清清楚楚。
若是引魂使现在出现,斩断我和林瑜之间的复礼限制,倒是能让我耳根少受点罪。
只是这些年兵灾和天灾连发死人太多,地府引魂使忙不过来,
只能留我这缕孤魂在人间继续受罪。因此,百日内我只能跟着林瑜,等待限制自动解除。
但庆幸的是,跟在他身边的两个月里我吸收了他不少的阳气,
复礼限制活动的范围已经由寸步不离到可以在王府内自由活动。我刚想再飘得更远一些。
猛地阮纭的声浪戛然而止,突然仓促结束。我勾了勾唇,
想不到他今日竟连半盏茶的功夫都没有就萎了,看来应是我的阴气削弱了他的阳气所致。
“三郎,我来帮你。”阮纭娇软响起,压抑着内心的急切,是明显的欲求不满。
我看不到密室里的春光,过了一会儿,密室内才传来了林瑜烦躁的语气。“吐出来,别弄了。
”哈哈哈哈,貌似是真的不行了。我忍不住笑出了声。阮纭似乎还不死心想要继续。
“你是听不懂人话吗?松开。”惹得林瑜暴怒大喊,半盏茶前的温柔荡然无存。
室内又是一片安静,等了一会儿才传出了阮纭嘤嘤嘤的抽泣声。漫漫长夜挺无趣的,
有好戏看又怎能错过。我改了主意,飘进密室。密室里林瑜已经穿好了里衣,站在榻边,
手拿着锦正要往阮纭一丝不挂的身上盖去。还未张口,阮纭就扯过他手里的锦被,翻身而起。
一张挂满泪水的脸,疾言厉色喊道:“三郎,你是不是后悔了。”“后悔什么?
”“后悔为了我,害了姐姐!”7林瑜同阮纭的事,是在我死后三天发现的。
下葬后他们又陆陆续续在密室里约会了好几次。
那间密室能从林瑜的书房通到王府另外一条街,阮府就在那条街上,只是我生前从不知晓。
这两个月里我在两人床第之欢间听到了许多生前不知道的真相。他爱的人从来都不是我。
两年的夫妻生活不过是应付,甚至让他觉得索然无味,在我面前的温柔体贴,
也都是逢场作戏。娶我,是为了得到太后青睐。今上三岁登基,太后垂帘,成王摄政,
共辅幼帝。如今已过了二十二载,天子早已冠成。朝堂却形成了两大政治派别,
太后派和亲王派,而天子并无任何实质权柄。朝野上下皆知,太后偏爱自己的亲子侄林琮,
希望其继承成王府的一切。按惯例,袭世子位者,为王府未来主人,任镇国军少将军,
但最终却是林琮为少将军,而林瑜为世子。这是成王和太后多年周旋博弈的结果。
可林瑜却不甘心,不甘心只做个空有名头的王府世子.所以他拼死向太后求娶了我,
让我成为助他登上青云高位上的一块垫脚石。婚后他取得了太后信任,在禁军中谋得一职,
不再是空有美貌的花瓶世子。得知真相时,我只觉得可笑,而如今却是有了杀人的心。
是他杀了我,竟是他杀了我!我冲了上去,两只手不停想扼住他的脖子,掐死他。
一遍、两遍、三遍……除了空气,什么都抓不住。我强行逼迫自己冷静,
盯着林瑜那张过于苍白的又太过于昳丽的脸。有一丝丝淡淡的阴气缠绕额间。
一张报复的蓝图在我心里勾勒,只要我有足够的耐心,终有一日定能要了他的性命。
8我安慰自己,逃离了密室,心中却始终萦绕不开那股恨意,浑浑噩噩在王府内四处飘荡。
咚……咚!咚!寂静的黑夜传来了更夫敲梆的更声。我猛然清醒,一抬头,
白首园三个字落入眼里。昔日的种种浮现在眼中,心里直泛恶心。我想挥手打落,
紧闭的门却嘎吱一声开了,出来却是林瑾身边的护卫,林小海。这么晚了,
他怎么会出现在这?我狐疑着,顺着他关门的视线看到园内的屋子里竟亮着烛光。
是谁在里面不言而明。我飘了进去,扑面而来落雪里带着淡雅的清香。皇京地处南方,
常年无雪,是屋前那株高大茂盛的梨树又开了花。我抬头,又是一阵风过,
胜雪的花瓣映着中天溶溶冷月簌簌而下,恍然间似看了场风花雪月。我最爱梨花。
彼时我们坐在宫内青莲池旁的梨树下,他说:“我家离园里的梨树,
花开得比宫里的梨花开得还要好。”我哈哈大笑,说他年纪不大,大话倒是张口就来,
宫里的一切哪样不是顶好的,就算是王府那是也比不上的。他斜乜了我眼,“你来我家,
我带你看。”“去就去。”我抱着看笑话的态度来了王府的离园中,而后被狠狠打脸。
离园中的那株梨树不仅花枝繁茂,花色似雪,更是比我见过的任何一株梨树的花开得都要好,
都要白。我叹服地绕着树看了一圈又一圈,嘴里不停地赞赏王府培育花木的花匠,
想让他帮忙引见。他回道:“你见过的。”“我见过?”顿时视线看向了他。春风熙和,
暗香浮动,满缀枝桠的白梨花被风飘落。那一幕我至今都记得。
他就站在黄昏的梨树下对着我笑,乌黑的发坠满了雪白的花瓣,眼眸中含着深藏不住的骄傲,
答得很是平常,“嗯,是我娘。”他总是暮气,很少笑得那么明朗,那么生动,
那么地让人心神悸动……9我愣愣地听着他说了冯侧妃和这座离园的故事。
冯侧妃出生在烨国北地边境线上的一座小村庄里,村子里有个风俗。
即在当年的第一场落雪后,全村的人会一起烹羊宰牛举村欢庆祈祷来年丰收,
所以雪一直都是冯侧妃童年记忆中最欢愉的存在。只是后来北地邻国朔月挑起争端,
那一村的人都死在了铁蹄和兵刃下,只有冯侧妃藏在族人的尸体下侥幸活了下来。
而后乞讨南下遇到人牙子,又不停被发卖,过着非人的生活。
直到遇到了救她脱离苦海的小姐。她很珍惜来之不易的安稳生活,所以她努力做事,
得了小姐的青睐,成为小姐身边最得力信任的丫鬟。之后小姐嫁人,
她便作为陪嫁丫鬟随小姐一同出嫁。小姐嫁的是烨国的皇帝,她本以为这辈子都会老死宫中,
却不想发生了意外赐给成王,成为侧妃。“可无论是宫女,还是侧妃,
阿娘都绝不可能再回到北地,雪也变成了奢望。”说到这他眼里的光暗了下来,
“这座离园便是我娘唯一能看到雪的地方。”梨音同离,有离别,分离之意。
我想当初冯侧妃将偏园取了这个字,心下应是有千回百转的不舍。
只是后来我病情加重需要静养,林瑜便想起了府内这处这处最安静的园子。
我本想拒绝却又拗不过他一再要求,最后还是他去信给林瑾征得了他的同意,我才搬了进来。
搬进来后他又不喜离字,说不吉利,又再次去信林瑾得了同意,缠着我另改新名。
我本想取名白雪两字来应园中之景。他却温柔地对着我笑:“白雪虽好,却不如白首之名,
应景更应你我之好。”我心头猛然一动,脑海中闪过的是昏黄光线下暮雪青丝里,
惊鸿一瞥后那抹深深的笑。一生一代一双人,愿得白首不相离。那是我当下冒出的两句心声。
后来我送出去的那把生辰弓,取名为如愿。10我停住了自己胡乱翻转的思绪,
辗转落入此刻的轩窗灯影里。我上前,灯里的人孤寂、落拓,
阒黑的眸一瞬不瞬盯着桌上的两支玉簪。眉唇紧拧,
所有的表情都清晰地印着很不高兴几个字。屋里的光线不强,
我仅认出了其中一枝簪是林瑜那个狗东西在新婚之夜送给我的礼物。那夜,
他穿着华美的喜服却去了我手中的锦扇,深情款款地说道:“我知与我成亲非你所愿,
可能娶到你,已然是我今生之幸。”接着他就从怀里拿出这枝羊脂白玉簪别在我头上。
再道:“从前你最喜的那支玉梨花簪丢了,我本来想寻块同样质地的石料重刻花簪,
却怎么都寻不到相同质地的玉石。”“我想这也许就是天意吧!”“阿缨,
我自知取代不了你的从前,却也想同你有新的开始。”……刚冲淡的恨意再次翻涌开来。
难道天意就是让你杀了我,然后和你的小浪纭在密室中肆意地翻红浪!
眼前簪子让我觉得碍眼,我恨不得将它同林瑜一道碾为齑粉。心念刚动,有人比我快了一步。
啪……羊脂玉簪被狠狠摔在墙上,瞬间粉碎。他似乎出了心中那股憋闷许久的恶气,
冷然一笑。拿起桌上那唯一的簪子,轻挲着玉石上缠绕的金线,狠厉的模样里生出丝丝眷恋。
只听他低声轻喃:“阿缨,这一切都不是真的,对吗?你会回来的,对吗?”而后开始抽泣。
我的心口阵阵发酸生疼。金灿灿的丝线映着明晃晃的火烛,
隐没在簪首那处碎了一角的玉梨花若隐若现。熟悉的纹样,
似月般莹透的簪子蓦地往我记忆里狠撞了一下。曾几何时我是那么地珍重它,
将它视为珍宝放在妆奁中,除了生辰极少佩戴。那换了面目的一溪月。
华贵的金线鬼斧神工地裹住了断横裂隙,那碎了一角的形状如芳菲落尽,
连化腐朽的神工巧匠都无能为力。我怔然地伸出手,想要去摸一摸那张泣不成声的脸,
手却穿过他的脸颊。天人永隔……阿瑾,我回不去了。我们再也回不去了!11翌日。
没想到我杀林瑜的机会来得如此之快。今晨他被成王打了三十军棍,
现下正像条死狗一样趴在床上呻吟。事发缘由听王府里下人议论,是在六更天时,
也是我离开后的一个时辰。王府的巡卫听到了林瑜书房内传来婢女的呼救声,
而后救下了晕死在地的林瑜。之后又经王爷随身军医诊症,
证实林瑜是纵欲无度导致的气虚晕厥。成王行事作风向来以清正守节,言出法随标榜。
按烨国律,夫丧妻者三月内需着素服,不得行房事或参与任何形式的娱乐,违律者杖百,
游街三日。现下林瑜做了这等下作且于礼法不合的龌蹉事,他自是极怒。当即命人灌下汤药,
下令杖责三十,分三日执行刑罚。虽然王此举存在偏私袒护之意,
但于我杀林瑜而言却是大有裨益。人生而为阳,死为阴。想要伤他性命,
于我而言唯一的办法就是削弱他的阳气。这也是此前我在密室里时想到唯一能杀了他的办法。
只是我的魂魄太过羸弱,没有办法一直不停输送阴气削弱他的阳气,
只能靠不断积累伤害来要他的命。原本这项计划,得耗费我不少时日。却没想到他自己作死,
八成是为了哄阮纭高兴,又再次与她浪沉沦才会身体承受不住而晕倒。身体有亏,
又受了军杖,整个人都受到了极大重创。若我这时在最大极限的输送阴气,
那他的死期也就不远了。12报复的快感在我身体里蔓延。三天了,
林瑜都日日游走生与死的边缘挣扎。这边药刚灌下去,那边的棍棒就打了上来,
阴气在他身体各处作祟,生机被毁损了大半,背上的伤也未痊愈。今日更是发起了高烧,
整个人陷入昏迷状态。我恨恨地盯着床上这个我曾经想要努力爱上却始终未爱上过的男子,
黑得泛青的发掩映着惨白无色的脸更显秾艳昳丽,
全然看不出是个半只脚踩进阎王殿门口的人。“你在这做什么?
”耳边倏然响起了稚嫩的稚子疑问好奇之声。玉石宫阶上坐着个泣不成声的小人儿。
小人儿抬眼,是个眉目俊秀,长得比她都漂亮的小胖墩。“不关你事!
”小人儿红着眼偏过脑袋,压着刚才教习嚒嚒训斥的委屈回答。小胖墩沉默了一会儿,
像是在思考什么,然后开口。“你别难过了,我这里有好吃的,吃了就不会难过了。
”小人儿心里骂了句傻子,仍旧没有理会,小胖墩却把一块酥饼递到她面前。
香甜的酥饼混着油脂的焦香猝不及防地窜入鼻尖,她定定看着那块花朵形状的酥饼,犹豫。
“你尝尝嘛,这是新月楼新出的百花酥,一口下去满嘴都是花香味,可好吃了。
”小胖墩以为她是不好意思,再次热情地邀请。小人儿看着他黑羽一颤一颤昳丽期待的眉眼,
无奈地叹了口气。只好将酥饼接过,将饼掰成两半,“你陪我一起吃吧。”“好呀。
”小胖墩狼吞虎咽的吃下了那半块酥饼,还不忘问小人儿味道如何。小人儿只好点头,
“好吃的。”小胖墩得意极了,笑得露出颗尖尖的虎牙。“有品位,
以后你就是阿瑜的好朋友了,如果宫里再有欺负你,你就告诉我,我帮你揍他们。
还有这百花酥,你以后想吃多少有多少!”这便是我与林瑜的初识。其实我不爱食甜,
此前吃过百花酥的我只是对美好的善意不想拒绝,便故作友好地将饼分一半给他。
却不曾想换来了一个整日跟在我身后的小尾巴。13小尾巴信守承诺,
把欺负我的教习嬷嬷都修理了个遍。事后他被太后训诫思过还不知怕,
更是得意洋洋地过来向我炫耀帮我报了仇。那时我就想,还真是个傻的。白驹过隙,
我和小胖墩就这样成了吃喝玩乐样样不落又彼此关照的好友。
而小胖墩也长成了风华绝代皇京的美人,如名瓷美玉,还有被人取了个诨名,玉公子。
玉公子这诨名,说白了是讽刺他只是个长得好看的花瓶公子。幼帝登基第十六年,
多次扰乱北地边境的朔月终被镇国军所平。二十二岁的林琮在军中声望渐盛,
太后一派以军功为由上书策封其为镇国军少将军,任车骑将军。镇国军少将军只是一个名头,
但这个名头却是通往王府和镇国军继承人的康庄大道。成王未正面回应,
只提出要立同为嫡子的林瑜为王府世子。双方相争不下,一时成为皇京中热议话题,
林瑜玉公子的诨名,也是那时而来。几乎所有人都唱衰他,就连赌庄设局押宝,
他也是超高赔率的一方。我还替他不平,责怪那些人凭什么给他取这样羞辱人的诨号,
还看笑话似的开局押宝。他却不在意地笑说,玉公子挺好的,
一听就是个风流不羁又潇洒的名号。我不信他的鬼话,脱口而出:“难道王位、军权,
你一个都不想要?”他猛地像看智障一样地看着我。“阿缨,
你是不是在老巫婆身边待太久了,怎地越来越俗气!”伸手报复似地揉乱我的刘海。
又认真道:“我才不要和你,和大哥一样做个被人摆弄的木偶,
我什么世子将军统统都不稀罕,做个逍遥自在的玉公子就很好。
”那时我分明看到他眼里热切期盼的光,不似作假的心生向往。那为何,
当初不愿染是非的少年郎,会变成这般争名逐利,不择手段!又为何,为了名利娶我,
又反过来杀我?就算是为了阮纭,他若以子嗣为由纳妾,我根本无法拒绝。
毕竟我小产时太医就言明需调养数年才好在育子嗣,
他犯不着为了一个什么都不是的阮纭冒险杀了我这个的助力。可此刻我已无力再想。
仇恨在我内心盘踞生根,寸寸催促着我,杀了他,杀了他。杀了他,过往的一切都将消散。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