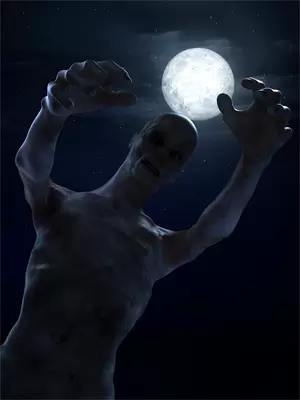
唐欣和许丞的家只隔了一道爬满爬山虎的院墙。从穿开裆裤的年纪起,
两人就共享着同一片蝉鸣与槐花香,又一前一后走进同一所小学、初中、高中,
像两条被命运牵在一起的平行线,始终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。
许丞是那种典型的“别人家的孩子”,成绩拔尖,话却少得可怜。他的冷淡像一层薄薄的冰,
覆盖在少年清隽的眉眼间——课间时总独自坐在座位上刷题,
放学路上戴着耳机听不见旁人招呼,连对门阿姨递来的烤红薯,也只是微微颔首,
接过时指尖轻触,道声“谢谢”便转身离开,礼貌得像在完成某种既定程序。
可就是这份疏离里的分寸感,在高三那个兵荒马乱的夏天,突然在唐欣心里炸开了花。
是某次模拟考后,她对着错题本发呆,他恰好经过,
冷不丁丢下一句“辅助线画错了”;是晚自习突降暴雨,她没带伞,他撑着伞从她身边走过,
伞沿悄悄往她这边偏了半寸,雨水打湿了他的肩膀,他却像没察觉;是走廊里迎面撞上,
他伸手扶了她一把,掌心温热,眼神掠过她泛红的脸颊时,快得像错觉。
那些被忽略了十几年的细节,忽然有了温度。她开始在人群里下意识地找他的身影,
会因为在食堂和他排在同一列而心跳加速,甚至偷偷数过他解题时转笔的频率。
这份心思像藤蔓,在日记本的字里行间悄悄蔓延,缠得她既心慌又隐秘地欢喜。
查录取结果那天,唐欣的手指在键盘上悬了半天,输入准考证号时指尖都在抖。
当“A大新闻媒体学院”几个字跳出来时,她还没来得及欢呼,
目光就被隔壁网页上的名字钉住了——许丞,A大工程设计学院。
窗外的蝉鸣突然变得格外响亮,阳光透过纱窗落在录取通知书的烫金校徽上,
晃得她眼睛发酸。她抱着枕头滚到床上,想起小时候爬院墙时,总能看见隔壁阳台上,
那个安静看书的少年。原来有些缘分,真的会像院墙上的爬山虎,不管经历多少个季节,
总会顺着时光的脉络,悄悄爬向同一个方向。往后的日子,
他们或许还会在图书馆的转角遇见,在教学楼的林荫道上擦肩而过。只是这一次,
唐欣攥着口袋里的学生证,心里藏着一个更清晰的念头:这四年,她想离那层薄冰,
再近一点。大学的梧桐叶黄了又绿,唐欣的暗恋像藏在树洞里的秘密,被风一吹就簌簌作响,
却始终没勇气让当事人听见。她摸清了许丞的规律:每周三下午三点会去设计院的模型室,
背着黑色双肩包,
装着画到一半的图纸和一支磨得发亮的金属圆规;周五晚上常泡在图书馆三楼的机械工程区,
靠窗的位置总能看见他——指尖捏着铅笔在草稿纸上划动,侧脸被台灯照得轮廓分明,
连睫毛投在眼睑上的阴影都带着规律的节奏。唐欣开始制造各种“巧合”。
她会算好时间去三楼借专业书,抱着一摞《新闻采访与写作》经过他身边时,
故意让书本发出轻微的碰撞声,
期待他能抬眼扫过来哪怕一秒;会在设计院楼下的奶茶店点单,
听见店员喊“许丞的冰美式好了”,就立刻说“我也要一杯一样的”,
只为接过杯子时能和他的指尖短暂相触——他的指尖总是凉的,像他的人一样。
她的手机相册里存着三十七条关于他的碎片:军训时他被晒红的后颈,
运动会上他冲过终点线时扬起的衣角,甚至有次他在黑板上解题,
她偷偷拍下的、写满公式的背影。这些照片从不示人,只在深夜躺在床上时,
被她放大又缩小,像在反复摩挲一件易碎的珍宝。转折发生在大二的跨学科交流会上。
唐欣作为新闻社代表去采访优秀学生,手里攥着写好的提纲,走到工程学院展台时,
脚步突然定住了。许丞正站在一个玻璃展柜前,低头给一个穿白裙子的女生讲解模型。
那女生是建筑系的林溪,唐欣在新生晚会上见过,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,
说话时总带着软软的尾音。此刻她正指着模型上的承重结构,语气里满是好奇,
许丞听得极认真,原本总是抿成直线的嘴角,竟微微松开了些。
“这里的榫卯结构角度改了三度,能减少百分之十五的应力损耗。”他的声音不高,
却带着唐欣从未听过的耐心,甚至伸手拿起一根细小的模型构件,演示给林溪看。
指尖相碰时,两人都没避开,林溪笑得更甜了,他也没像对别人那样立刻收回手。
唐欣举着相机的手突然有些抖,取景框里的画面晃了晃,最终只拍下一片模糊的光斑。
那之后,她见过他们一起去实验室,林溪抱着图纸走在左边,许丞拎着工具箱走在右边,
两人偶尔低声说句话,步伐都透着默契;见过许丞在食堂帮林溪占座,
餐盘里放着她爱吃的糖醋里脊——那是唐欣观察了三年才记住的喜好,
而他似乎轻易就知道了;甚至有次在教学楼门口,看见林溪踮脚帮许丞拂去肩上的落叶,
他微微低着头,眼神里的温和几乎要溢出来。原来他不是不会笑,
只是笑容不给她;不是不懂照顾人,只是那份细心与别人有关。唐欣开始慢慢后退。
她删掉了手机里所有关于他的照片,把那本记满他作息的笔记本锁进了柜子最深处,
路过设计院时会刻意绕开那条栽满银杏树的路。有次在图书馆遇见,她抱着书低头快步走过,
听见身后传来他和林溪说话的声音,脚步没停,心却像被什么东西轻轻蛰了一下,不疼,
却泛着密密麻麻的麻。大三那年冬天,唐欣在朋友圈刷到林溪发的照片:雪地里,
许丞站在圣诞树旁,手里拿着一个包装精致的礼物,脸上是她从未见过的、浅浅的笑意。
配文是:“谢谢许同学的圣诞礼物呀~”唐欣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,然后默默点了个赞,
退出了朋友圈。窗外的雪下得很大,她想起高三那个暴雨天,
他偏过来的伞沿曾让她心动了那么久。现在才明白,那或许只是他骨子里的礼貌,
就像他对谁都客气,却唯独对林溪,藏着不一样的东西。这场从十六岁开始的暗恋,
终于在某个飘雪的夜晚,轻轻落了幕。唐欣裹紧了围巾,往宿舍走,雪落在睫毛上,有点凉。
她想,或许该把心思收回来了,毕竟有些星星,就算踮起脚尖,也够不着的。
许丞结婚的请柬寄到唐欣公司时,她正在改一篇关于城市地标建筑的报道。
烫金的“囍”字落在米白色信封上,收信人栏写着“唐欣女士”,
字迹依旧是他惯有的清瘦利落,只是末尾多了个小小的“携妻林溪”。拆开请柬,
照片上的两人站在一片向日葵花田里,林溪穿着白色长裙,笑起来梨涡深陷,
许丞侧身望着她,嘴角弯起的弧度是唐欣从未在他脸上见过的柔软。
原来冰山真的会为某个人融化,只是她从不是那个持火把的人。婚礼定在初秋,
唐欣选了条香槟色连衣裙,化了淡妆。宴会厅里人来人往,
她远远看见许丞穿着西装站在门口迎客,林溪挽着他的手臂,两人偶尔对视一笑,
默契得像演练过千百遍。轮到唐欣上前时,她递过红包,笑着说“新婚快乐”,
许丞点头道“谢谢”,眼神平静无波,像在对一个普通老同学。席间,她看着他们交换戒指,
听着许丞在誓词里说“往后余生,风雪是你”,心里竟出奇地平静。散场时,
她在走廊遇见抱着捧花的林溪,对方笑着问“你是许丞的邻居唐欣吧?他跟我提过,
说你小时候总爬他们家院墙摘葡萄。”唐欣愣了愣,原来那些被她藏在心底的细碎时光,
在他那里,不过是一句轻飘飘的“小时候”。她笑着应道“是啊,那时候不懂事”,
转身离开时,脚步轻快了许多。那之后过了两年,唐欣在一次采访中认识了陈默。
他是家出版社的编辑,说话时总带着温和的笑意,会记得她不爱吃香菜,
会在她加班时送来热咖啡,会在她对着电脑皱眉时,轻轻揉她的头发说“慢慢来”。
他们第一次约会去看画展,陈默指着一幅印象派画作,认真听她讲新闻角度的解读,
眼神里的专注,像极了当年她看许丞解题的模样,只是这一次,那份专注是为她而来。
唐欣和陈默确定关系后,日子像被温水慢慢泡开的茶,泛起清浅的甜。
陈默知道她总熬夜改稿,会提前算好时间炖好银耳羹,装在保温桶里送到她公司楼下。
保温桶是淡蓝色的,和他常穿的衬衫一个颜色,唐欣每次掀开盖子,
都能看见冰糖在银耳羹里浮着,像碎在水里的星星。有次她赶一个突发新闻,
忙到凌晨两点才走出办公楼,远远看见路灯下站着个熟悉的身影——陈默裹着她的旧外套,
手里攥着个保温杯,见她出来,立刻把杯子递过来:“刚热的牛奶,喝了暖暖。
”他说话时带着点夜风里的凉意,眼神却亮得像落了星光。他们会在周末去逛早市。
陈默推着小推车跟在她身后,看她蹲在菜摊前挑番茄,手指捏着果实轻轻按,
嘴里念叨“要选这种带沙瓤的才甜”。他不插嘴,只在她起身时接过袋子,
自然地挂在车把上。路过卖糖画的摊子,唐欣盯着转盘上的小兔子看了两眼,
陈默就已经掏钱买了下来,递到她手里时笑说:“看你眼神都黏在上面了。
”糖画在阳光下晶莹剔透,甜得刚好不腻人,像他给的温柔,从不用力,却处处妥帖。
唐欣第一次带陈默回老小区,是去取换季的衣服。路过那道爬满爬山虎的院墙时,
她脚步顿了顿。陈默注意到了,顺着她的目光望过去,轻声问:“这里有故事?
”唐欣摇摇头,又点点头,最终只是笑了笑:“以前总爬这墙去隔壁摘葡萄。”陈默没追问,
只伸手牵住她的手,指尖温热干燥:“现在不用爬了,想吃葡萄我买给你,
超市里的阳光玫瑰甜得很。”那天晚上,陈默在她家厨房做饭,唐欣靠在门框上看。
他系着她的碎花围裙,背影不算挺拔,却让人觉得踏实。抽油烟机嗡嗡转着,
锅里飘出番茄炖牛腩的香气,唐欣忽然想起高三那个暴雨天,
许丞偏过来的伞沿曾让她心动了好多年。可此刻看着陈默低头尝汤的侧脸,她心里清楚,
那种心动像烟花,亮过就散了,而眼前的烟火气,才是能握在手里的暖。陈默求婚那天,
没选什么特别的地方,就在他们常去的江边。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