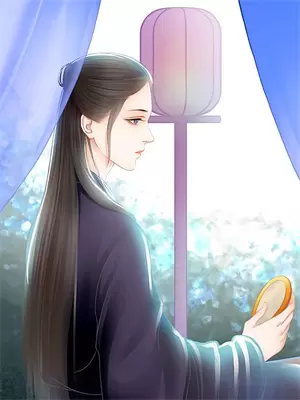1 禁忌之林咱这村子叫柳条沟,窝在山坳坳里,拢共就几十户人家。村东头老槐树底下,
是村里人闲扯唠嗑的地方。我打小就听老人们说,后山那片老林子,不能进,
尤其不能往深里走。为啥?说不清,反正祖祖辈辈都这么传下来的。“特别是太阳落山以后,
”我爷吧嗒着旱烟袋,眯缝着眼说,“那林子里有东西,不能看,更不能盯着瞧。
”我问:“是狼还是熊瞎子?”我爷摇摇头,烟锅子里的火一明一灭:“不是那些活物。
是……别的啥。反正你记着,要是万一非得从那边过,听见啥动静都别回头,
觉着背后有人瞅你也别转身,尤其,千万千万别抬头往树顶上看。”我那时候小,八九岁,
正是皮实又好奇的年纪。我爷越这么说,我心里越像有只小猫在挠。后山那片林子,
从村子这边望过去,黑压压的一片,白天看着就阴森,晚上更是安静得吓人。有一回,
我跟邻居家二胖打赌,赌他那个漂亮的玻璃弹珠。他说谁敢在傍晚靠近老林子边缘,
把那块歪脖子树上系的红布条扯下来,弹珠就归谁。那红布条不知道是哪年哪月谁系上去的,
风吹日晒,都快成灰白色了。为了那颗弹珠,我豁出去了。那天傍晚,天擦黑,
西边还剩一丝丝亮光。我猫着腰,顺着田埂往后山溜。越靠近那林子,心里越发毛。
周围的虫鸣好像都停了,静得只能听见我自己噗通噗通的心跳声。
歪脖子树就在林子外边十几步的地方,孤零零地立着。我小跑过去,踮起脚就去够那布条。
布条系得死紧,我使劲一拽,没拽动,反而自己脚下绊了一下,一屁股坐在地上。就在这时,
我听见林子里传来一阵“沙沙”声,不像风吹树叶,倒像是……有人拖着脚在落叶上走。
我浑身汗毛都竖起来了,猛地想起我爷的话——别回头!我手忙脚乱地爬起来,
眼睛死死盯着地面,用尽吃奶的力气往村子方向跑。跑出去老远,
我才敢稍微偏头用眼角余光扫了一下。暮色沉沉,那片林子像一头巨大的、蹲伏的野兽,
那棵歪脖子树模糊的影子,好像一个歪着脑袋的人。我没拿到红布条,自然也没得到弹珠。
还把裤子磕破了,回家被我娘结结实实揍了一顿。我没敢说去后山的事,只说是摔沟里了。
2 老棍之死从那以后,我好几年都没再靠近过后山。村里人也依旧遵守着那条老规矩,
没人去触那个霉头。直到我十六岁那年夏天,出事了。出事的是村西头的王老棍。
王老棍是个老光棍,平时不爱说话,就喜欢喝点小酒。那天他去邻村喝喜酒,回来晚了。
按理说,从邻村回柳条沟,绕着后山脚走大路,得多走半个时辰。王老棍大概是酒劲上来了,
图省事,想抄近路,直接从后山那片老林子穿过来。第二天晌午,
有人发现他躺在村口的老井边上,浑身冰凉,早就没气儿了。他身上没伤,衣服也没破,
就是脸色煞白,眼睛瞪得溜圆,嘴巴微微张着,像是看到了啥极其吓人的东西。最怪的是,
他的姿势,他是面朝下趴着的,但那个脑袋,硬生生扭了一百八十度,脸朝着天,
后脑勺贴着地。发现他的人吓得连滚带爬去喊村长。村里人都围了过来,议论纷纷。
有老人就说,这是撞见林子里那东西了,坏了规矩,看了不该看的。我挤在人群里,
看到王老棍那扭曲的脖子和圆睁的眼睛,胃里一阵翻江倒海,晚上做的梦都是他那张脸。
王老棍就这么埋了。没请和尚也没请道士,村长带着几个壮劳力,
草草把他葬在了村外的乱葬岗。下葬的时候,天色阴沉沉的。打那以后,
村里关于后山林子的传言就更邪乎了。大人吓唬哭闹的小孩都说:“再哭!
再哭就把你扔后山老林里去!”小孩立马就闭嘴了。日子还得过,地里的活儿不能停。
但后山那片影子,好像更重地压在了每个柳条沟人的心上。又过了几年,我成了家,
有了自己的娃。我以为这辈子就会像祖辈一样,在这山坳坳里种地、过日子,
守着那些老规矩,平平安安到老。3 外来者的悲剧可是,外面来人了。来的是一男一女,
开着我们从来没见过的吉普车,扬起的尘土老高。男的看着三十多岁,戴着眼镜,斯斯文文,
说是省里什么民俗研究所的,姓陈。女的是他学生,姓林,拿着个小本子不停地记。他们说,
是来收集我们这一带的民间故事和风俗习惯的。村长接待了他们,
安排在村委会那空房子里住下。村里人都好奇,围着那吉普车看稀奇。陈老师很会说话,
给小孩发糖,跟老人敬烟,没几天就跟一些人混熟了。他很快就听说了后山林子的传说。
出乎我们意料,他非但不怕,反而显得特别感兴趣。他找到村里几个上了年纪的老人,
包括我爷,反复地问关于林子的事。问那里面到底是啥,为啥不能看,
祖上有没有人真的看见过之类的。老人们都说得含糊其辞,
翻来覆去就是我爷说过的那套——有东西,不能看,看了要倒霉,王老棍就是例子。
陈老师推推眼镜,眼睛发亮:“这很可能是一种古老的禁忌信仰,
背后也许有历史或环境的原因。那片林子,说不定保存着非常原始的生态或者文化痕迹,
很有研究价值。”他跟村长商量,想进林子看看。村长一听,脸都白了,
连连摆手:“使不得!陈干部,这可万万使不得!那地方邪性,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话,
不能不当真啊!王老棍的惨状您没见着,我们可是都亲眼看到的!”村里其他人也纷纷劝阻。
陈老师和他学生却笑了,那是一种不相信、觉得我们愚昧的笑。陈老师说:“老乡们,
现在是科学时代了。那些传说,很可能是对某些自然现象或者危险动物的误解。
我们进去考察清楚,对村子也是好事嘛。”他执意要去。那天早上,天气挺好,
太阳明晃晃的。陈老师和小林背着包,包里装着相机、笔记本,
还有指南针和一根长长的棍子。村里好多人都聚在村口,默默看着他们。我爷蹲在槐树底下,
闷着头抽烟,最后忍不住站起来,走到陈老师面前:“陈同志,听我老汉一句劝,别去。
那林子……它不吃你们外面人那一套啊。”陈老师客气但坚定地笑了笑:“老爷子,放心吧,
我们有准备。”他们还是走了,朝着后山那片黑压压的林子走去。
我看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林子的边缘,心里莫名地有些发慌。一天过去了,两人没回来。
到了晚上,还没见人影。村长坐不住了,召集了十几个青壮年,打着火把,
准备进林子边缘找找看。我本来不想去,但我爹踹了我一脚,说大小伙子躲后面像什么话。
我也只好拿了根棍子,跟在队伍最后面。我们不敢深入,就在林子边上一边走一边喊。
火把的光亮在浓密的树木间显得很微弱,只能照亮脚下一小片地方。林子里面比外面黑得多,
也冷得多,那种安静让人心里发毛。我们的喊声在里面回荡,传出老远,却没有任何回应。
找了大半夜,啥也没发现。村长怕再出事,只好让大家撤回村子。第二天,
正当我们商量要不要去乡里报告时,小林回来了。她是自己走回村子的,
浑身衣服被刮得破破烂烂,脸上、胳膊上全是血道子。她眼神直勾勾的,
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什么。我们围上去,她像是看不见我们,
地、用一种极其惊恐的语调喃喃:“不能看……不能看……树……树顶上有……”话没说完,
她身子一软,晕了过去。我们把她抬回村委会,找了村里的赤脚医生给她看了看。
身上都是皮外伤,但人一直昏昏沉沉,发着高烧,说胡话。陈老师没有回来。
小林在第三天凌晨,突然醒了。她睁着眼,直直地看着屋顶,眼神里全是恐惧。
她断断续续地跟守在旁边的村长说了他们进林子后的遭遇。他们说,一开始很顺利,
林子就是普通的林子,除了树密一点,没啥特别的。他们越走越深,拍了些照片,
采了些植物标本。后来,天快黑的时候,他们发现了一处奇怪的地方。那里的树格外高大,
而且排列得有点怪,围着一小片空地。空地上寸草不生,只有中间立着一块半人高的黑石头,
石头表面光滑得像抹了油。陈老师很兴奋,围着那石头转悠,说这可能是古代祭祀的遗迹。
就在这时,他们听见头顶的树冠里传来一阵响动,很大声,像是很多爪子在挠树皮。
小林吓得要死,想起村里的告诫,拉着陈老师想走。陈老师却抬头往上望去,
嘴里还说:“可能是某种大型鸟类或者猿猴……”小林说,
她当时下意识地也跟着抬头看了一眼。“那是什么……是什么……”小林浑身发抖,
声音嘶哑,
大很大的……白色的脸……没有鼻子……只有两个黑窟窿眼睛……它在笑……”她说到这儿,
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,又晕了过去。等她再醒来,发现自己躺在林子边缘,天已经蒙蒙亮了。
她挣扎着爬起来,陈老师却不见了。她不敢回头,不敢停留,拼了命地跑回了村子。
村里人听完,一片死寂。恐惧像冰冷的河水,瞬间淹没了所有人。陈老师,
大概率是回不来了。乡里后来来了人,组织民兵进林子搜救过两次。第一次什么都没找到。
第二次,他们在林子深处发现了陈老师的背包,里面的东西散落一地,相机摔得粉碎。
背包旁边,还有一只鞋。人,活不见人,死不见尸。自那以后,后山那片老林子,
成了我们柳条沟更加坚固的、谁也不敢触碰的禁忌。连提,都很少有人提了。
4 夜半惊魂小林老师被乡里来的吉普车接走了,走的时候还裹着厚厚的毯子,
眼神直勾勾地盯着车窗外面,嘴里嘀嘀咕咕的,谁也听不清她说啥。村里人站在路边,
默默地看车开远,扬起的尘土落在每个人心头,沉甸甸的。后山那片林子,
这下是彻底成了活人勿近的鬼地方。连平时最淘气的半大小子,
也不敢再提去林子边沿摸鸟蛋的事了。家家户户都严厉告诫孩子,谁要是敢往后山跑,
腿打断。日子好像又回到了从前,但又不一样了。以前是模糊的恐惧,
现在是血淋淋的例子摆在眼前。王老棍的死,陈老师的失踪,小林老师的疯,像三块大石头,
把柳条沟压得喘不过气。村里开始流传一些更细碎的说法。有人说,那林子里住的是山魈,
专门喜欢把人脑袋拧过来看后背。有人说,那是早年枉死的人化的厉鬼,怨气不散,
就藏在树顶上。还有老人偷偷念叨,说那不是啥鬼啊怪的,是更老、更说不清的东西,
比咱们村子的历史还久,是这片土地自带的“毛病”。我爷从那以后,烟抽得更凶了,
常常一个人坐在门槛上,望着后山的方向一坐就是半天。我娘和我婆娘更是紧张,
天一擦黑就赶紧关门闭户,生怕有啥东西顺着门缝溜进来。大概过了个把月,一天夜里,
我起来撒尿。农村的茅房都在院子外头,我迷迷糊糊拉开屋门,一股凉风灌进来,
让我打了个激灵。院子里月光挺亮,照得地面白晃晃的。就在我准备往茅房走的时候,
眼角余光好像瞥见院墙根那儿有个黑影动了一下。我汗毛一炸,睡意全无,猛地扭头看去。
是邻居家那条叫大黑的老狗。它平时挺凶的,见生人就吠,这会儿却夹着尾巴,
喉咙里发出低低的呜咽声,身子紧紧贴着墙根,脑袋却以一个极其别扭的姿势,
使劲向上仰着,那双在夜里发绿的眼睛,死死地盯着我家房后那棵老榆树的树顶。
我顺着它的目光往树顶上看。月光被茂密的枝叶切得粉碎,树顶上黑黢黢一团,啥也看不清。
大黑就那么盯着,呜咽声越来越小,身子开始发抖,最后竟然瘫软在地上,屎尿齐流,
骚臭味顺着风飘过来。我吓得魂飞魄散,裤裆差点也湿了,连滚带爬地冲回屋里,
死死插上门栓,背靠着门板大口喘气。我婆娘被惊醒,问我咋了。我嘴唇哆嗦着,
半天才挤出一句:“没……没啥,大黑……大黑疯了。”我没敢说大黑看树顶的事。那一夜,
我俩都没再睡着。第二天一早,就听见邻居在骂街,说他家大黑死了,就在我家院墙根底下,
身上没伤,眼睛还圆瞪着,像是吓死的。邻居觉得晦气,骂骂咧咧地把狗拖出去埋了。
只有我知道大黑昨晚看见了什么。或者说,它想看见什么,又或者,它被什么给“看”了。
我心里那股凉气,一直到太阳升得老高,都没暖过来。开春的时候,村里来了几个测量员,
说是要规划修路,测量山势地形。他们拿着奇怪的仪器,在村子周围比比划划。
他们自然也注意到了后山那片格外茂密、地势也显眼的的老林子。
带队的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,姓赵,嗓门很大。他指着林子对村长说:“老哥,
这片山窝窝就你们这林子长得最好,要是修路从这边上过去,取材也方便,能省不少钱哩。
”村长一听,脸都绿了,赶紧摆手:“赵工,使不得!万万使不得!那林子动不得!
”赵工哈哈一笑,不以为然:“咋?还有老虎豹子不成?现在野生动物都保护着,咱不砍它,
就从边上过,没事!”村里人围上来,七嘴八舌地劝,把王老棍、陈老师的事都说了。
赵工和他手下的人听着,脸上那表情,跟当初陈老师一模一样,
是一种混合着好奇、不以为然,甚至有点觉得好笑的神情。“老乡们,这都是巧合,
得讲科学!”赵工拍着胸脯,“再说,我们这么多人,带着家伙呢,怕啥?”他们不信邪。
第二天,赵工就带着两个人,要去林子边上做初步测量。村长拦不住,
只好派了我和另外两个年轻后生跟着,嘱咐我们千万只在最外边,别往里走。
我们仨心里一百个不情愿,但又没办法。跟着赵工他们来到林子边缘,
就是当年我扯红布条的那棵歪脖子树附近。林子还是那个林子,安静得让人心慌。
赵工他们忙活起来,摆弄仪器,立标尺。我和另外两个后生紧紧靠在一起,
眼睛死死盯着那片幽暗的林子深处,手里攥着出发前老人给的,说是能辟邪的桃木棍子,
手心全是汗。一切顺利,测量快结束了。赵工拿着个本子记录数据,
嘴里还念叨着:“这林子确实有点怪,磁场好像不太对劲……”就在这时,
一个年轻的测量员,大概是想找个更好的观测点,往林子边缘多走了几步,
靠近了一棵特别高大的老松树。他无意间抬了下头,好像是在看树冠的高度。
就在他抬头的一瞬间,我清楚地看到,他整个人猛地僵住了,
手里的记录本“啪嗒”一声掉在地上。他保持着仰头的姿势,一动不动,像是被施了定身法。
“小张?咋了?”赵工也发现了不对劲,喊了一声。那个叫小张的测量员没有回答。
他的身体开始剧烈地抖动起来,像打摆子一样。然后,
他发出了半声极其短促、像是被掐住脖子的吸气声,猛地抬起双手,死死捂住了自己的眼睛,
手指头因为用力而扭曲。“啊——我的眼睛!眼睛!”他凄厉地惨叫起来,
但那声音不像从他喉咙里发出的,更像是从胸腔里挤出来的,闷哑而痛苦。我们全都吓傻了。
赵工和另一个测量员想冲过去拉他。“别过去!”我不知哪来的勇气,嘶声喊道,“不能看!
快低头!拉他回来!别抬头!”赵工他们也慌了神,听到我的喊声,下意识地低下头,
冲过去一人一边架住小张的胳膊,拼命把他往外拖。小张已经完全软了,像个破麻袋,
被拖着走,双手还死死地抠在眼睛上,指缝里渗出血来,嘴里发出嗬嗬的、不成调的怪声。
我们几个连滚带爬,几乎是逃命一样冲回了村子。小张被紧急送去了乡卫生院。后来听说,
他眼睛没瞎,但医生说受了强烈的刺激,视力严重下降,而且精神出了问题,
见不得密集的枝叶,一见就发疯。修路的事,自然也没人再提从后山走了。
赵工他们很快就撤走了,走的时候,赵工那张大嗓门的脸,白得跟纸一样。经过这事,
村里那不能看的禁忌,不再是老人们嘴里虚无缥缈的传说,
它变成了小张测量员捂着眼睛惨叫的声音,变成了指缝里渗出的血,
变成了我们每个人心里一道血淋淋的、不敢触碰的伤疤。俺叫李铁山,柳条沟土生土长的,
爹娘起这名字,这些年,我感觉自己就像山脚下的一块石头,
被那林子里的阴影压得喘不过气。小张测量员那事过去后,村里更是风声鹤唳。
以前只是天黑不敢去,现在是大白天,也没人愿意靠近后山脚下那片地了,
连带着那附近的几块田都差点荒了。村里辈分最高的七太公,九十多岁的人了,
平时糊涂的时候多,清楚的时候少。那天傍晚,他让人扶着来到老槐树底下,
浑浊的老眼望着后山,嘴里念念叨叨,说那不是山魈,也不是厉鬼,是“守护灵”,
是更古早的时候,守着这片山川的“灵”,嫌咱们人吵着它了,坏了它的清净。“不能看,
是规矩,”七太公哆哆嗦嗦地说,“看了,就是坏了规矩,
它就要发怒……要带走坏了规矩的人……”有人问:“太公,那到底是个啥‘灵’啊?
长啥样?”七太公摇摇头,眼神里透着恐惧:“不知道……没人知道……知道的,
都回不来了……老辈子传下的话,只看地,莫看天,
尤其……莫看那树梢顶……”这话说得没头没尾,却让大伙儿心里更沉了。一个不知道是啥,
但确实存在,而且脾气不好的东西,比知道是啥更吓人。
5 石头的噩梦日子就这么提心吊胆地过着。直到我家娃子出了事。我娃子小名叫石头,
八岁,皮实,跟他爹我小时候一个样。夏天河里涨水,我们都不让孩子去河边玩。
石头和他几个小伙伴,没地方野,不知怎么的,
就摸到了村子靠近后山的那片野草丛里抓蚂蚱。那天我下地回来,没看见石头,
我婆娘说跟狗蛋他们出去玩了。起初没在意,直到天快黑了,狗蛋他们哭哭啼啼跑回来,
说石头不见了。“我们……我们就在那边抓蚂蚱,”狗蛋吓得脸煞白,
“石头说他看见个特别大的花蝴蝶,往林子那边飞,他就去追……我们喊他,他不听,
跑着跑着就没影了……”我脑子“嗡”的一声,像被雷劈了。后山林子!我爷的话,
王老棍的死,陈老师的失踪,小林老师的疯,小张的惨叫……所有画面一瞬间全涌到我眼前。
“啥时候的事!”我一把抓住狗蛋的胳膊,力气大得把他捏哭了。“就……就下午,
太阳还老高呢……”我啥也顾不上了,抄起墙角的锄头就往外冲。
我婆娘在后面哭喊着追出来,被我爹死死拉住。“铁山!别冲动!喊上人!一起去找!
”我爹的声音也在抖。我哪里听得进去,石头是我儿子!我唯一的娃!我像头发疯的牛,
朝着后山方向狂奔。村里人听见动静,也都拿着家伙跟了上来,我爷和我爹跑在最前面,
脸色铁青。我们冲到那片野草丛,哪里还有石头的影子。只有他掉在地上的一只小布鞋。
“石头!石头——!”我嘶声力竭地喊着,声音在傍晚空旷的山野间回荡,带着绝望。
有人指着草地上一溜被踩倒的草痕,那痕迹,隐隐约约指向老林子的方向。我的血都凉了。
“不能进!天快黑了!进去就是送死!”有老人拦着。“那是我儿子!”我眼睛赤红,
推开拦我的人,就要往林子里冲。“站住!”我爷猛地一声暴喝,他死死盯着我,
嘴唇哆嗦着,“你想让石头回不来,你也回不来吗!”我僵在原地,
看着那片在暮色中越来越黑、像巨兽张开大嘴的林子,浑身的力量像被抽空了一样,
瘫软在地。那一刻,我恨透了这片林子,恨透了那不知道是啥的鬼东西,
也恨透了我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这该死的规矩!村里人点起了火把,但没人敢踏进林子一步,
只能在边缘声嘶力竭地喊。回应我们的,只有越来越浓的夜色和林子里死一般的寂静。
我婆娘哭晕过去好几次。我娘搂着她,也跟着掉眼泪。我爹和我爷蹲在地上,
吧嗒吧嗒地抽烟,火光映着他们沟壑纵横的脸,一片灰败。时间一点点过去,
希望越来越渺茫。就在所有人都快要绝望的时候,
林子边缘的灌木丛突然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响声。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,握紧了手里的家伙。
一个瘦小的身影,摇摇晃晃地从灌木丛里走了出来。是石头!他走路的样子很怪,
深一脚浅一脚,像个木偶。脸上、身上被划了不少口子,但看起来没受啥大伤。“石头!
”我狂喜地冲过去,一把将他紧紧抱在怀里,感觉到他小小身子的冰凉和轻微的颤抖。
“我的儿啊!”我婆娘也醒过来,扑过来抱着我们父子俩号啕大哭。村里人也松了口气,
围了上来。“石头,你跑哪儿去了!吓死爹了!”我检查着他身上,生怕少了啥零件。
石头抬起头,眼神直勾勾的,没有焦点,也不看我们任何人。他小脸苍白,
嘴唇没有一点血色。“爹……”他声音很小,带着颤,
“我……我追蝴蝶……后来……后来迷路了……”“没事了,没事了,回来就好,回来就好。
”我拍着他的背,心里那块大石头总算落了地。
“我……我听见有人叫我名字……”石头继续喃喃道,眼神还是空的,
“我就跟着走……走着走着……就出来了……”“谁叫你?”我爷猛地站起来,声音严厉。
石头被我爷吓了一跳,往我怀里缩了缩,
摇摇头:“不知道……听不清……好像……好像是从上面叫我……”上面?
所有人心里都是一咯噔。“然后呢?”我爷追问,语气急迫。
“然后……然后……”石头皱着小眉头,好像在努力回忆,
“我……我想抬头看……是谁叫我……”周围瞬间安静下来,连火把燃烧的噼啪声都听得见。
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“你抬头看了?”我爷的声音发紧。
没有……我……我害怕……记得太爷爷说过……不能往树顶看……我就……我就一直低着头,
跟着那声音走……”我清楚地听到,周围好几个老人同时长长地、如释重负地吁了一口气。
我爷蹲下身,第一次用那么温和的语气对石头说:“好孩子,你做得对,做得对……记住了,
以后不管啥时候,不管谁叫你,不管听见啥,都不能往那树顶上看,记住了吗?
”石头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。我把石头背回家,他很快就睡着了,但睡得极不安稳,
时不时惊悸一下,嘴里发出模糊的呓语。虽然石头回来了,身体也没啥大事,但我心里明白,
有些东西不一样了。那林子的阴影,不仅笼罩着柳条沟,现在,
也实实在在地压在了我儿子的心头,也许,一辈子都抹不去了。
而关于那“上面”呼唤名字的声音,更是成了村里人夜里不敢细想的噩梦。
它不再只是静静地待在那里,等着人触犯禁忌,它……似乎开始主动了。
6 马半仙的牺牲我们这儿的隔壁村有一个叫马半仙的人,据说能通阴阳,驱邪祟。
以前村里人有个头疼脑热、丢魂落魄的,也常去找他。这次石头的事,
加上之前接二连三的祸事,让村长和我爷下了决心,无论如何,得请他来瞧瞧,
哪怕只是求个心安。马半仙来得很快,是个干瘦的小老头,穿着件洗得发白的旧道袍,
眼睛不大,但看人的时候透着一股精光。他围着村子转了一圈,最后站在村东头的老槐树下,
眯着眼看向后山那片林子,半晌没说话,脸色越来越凝重。“好重的煞气,
”他捻着下巴上几根稀疏的胡子,喃喃道,“这东西……年头不浅了,不是寻常的孤魂野鬼。
”村里人围着他,大气不敢出。他让人准备了香烛纸钱,一只大公鸡,还有一碗清水。
就在老槐树底下,他摆开了阵势。点燃香烛,烧了纸钱,嘴里念念有词,声音忽高忽低,
也听不清念的啥。然后他提起那只大公鸡,手起刀落,鸡血滴进那碗清水里。说来也怪,
那鸡血滴进碗里,并不散开,反而凝成一缕,像条细小的红蛇,在碗底快速地盘旋游动。
马半仙盯着碗里的血,眉头拧成了疙瘩。他端起碗,朝着后山林子的方向,
猛地将血水泼了出去。血水泼出去的瞬间,平地忽然刮起一阵旋风,卷起地上的尘土和纸灰,
打着旋儿往林子的方向飞去。那风阴冷阴冷的,吹得人汗毛倒竖。马半仙身体晃了晃,
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他猛地回头,对村长和我爷说:“这东西……我送不走,也镇不住。
它不是外来的,是这地方‘土生土长’的,跟这片山,这片林子捆在一块儿了!
”“那……那咋办?”村长声音发颤。“只有一个法子,”马半仙喘着粗气,
眼神里带着一种近乎绝望的决绝,“我得进去,跟它谈谈‘规矩’。”进去?进那林子?
所有人都惊呆了。“马师傅,这可使不得!进去的人都……”我爷急忙阻拦。马半仙摆摆手,
打断他:“我知道风险。但不清不楚的‘规矩’,迟早害死更多人。我得去问问,
它到底要啥,这‘不能看’的界限,到底在哪!总不能一辈子提心吊胆,
连娃娃都不能安心出门!”他态度坚决,从随身带的布包里取出几道画好的黄符,
贴在自己胸前、后背,又拿出一串油光发亮的念珠挂在脖子上。“你们就在这儿等着,
不管听到啥动静,都别进来。如果……如果明天天亮我还没出来,”他顿了顿,
看了一眼黑黢黢的林子,“你们就……就别等了,想办法搬走吧,这村子,恐怕住不得人了。
”说完,他不再理会众人的劝阻,深吸一口气,头也不回地,
一步一步走向那片吞噬过数条人命的黑暗。我们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,
眼睁睁看着他那瘦小的身影被浓密的树木阴影吞没。林子边缘,仿佛有一道无形的界限,
他跨过去之后,连脚步声都听不见了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,月亮升起来了,又冷又亮,
照得林子边缘一片惨白。里面依旧死寂,什么声音都没有。我们不敢睡,也不敢离开,
就那么围着渐渐熄灭的火堆,默默地等着。夜里的露水打湿了衣服,冰凉。后半夜,